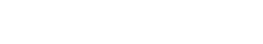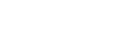纪念我的导师陈慰峰教授
陈老师是我的恩师。不思量,自难忘。
1996年,我从美国回来,投于陈老师门下。回想起来,那正是肿瘤免疫研究风起云涌,英才辈出的时代。1991年,Ludwig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Belgium Branch 所长Dr. Terry Boon领导的研究机构发现了第一个人类肿瘤抗原;1995年,Ugur Sahin教授和 Özlem Türeci教授 ,BioNTech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发表了开创性论文,报告了肿瘤抗原鉴定SEREX 方法,标志着肿瘤抗原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被称为肿瘤免疫学之父的Dr. Lloyd Old(Ludwig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在1996年,通过Ludwig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Melbourne Branch 的所长Tony Burgess教授,也是陈老师的老朋友,找到陈老师,希望能与中国合作进行肝癌肿瘤抗原的鉴定,开启了中国首个T细胞识别的肿瘤抗原鉴定研究。非常幸运的是,陈老师将这个项目交给了我。懵里懵懂地,我被陈老师拽进了肿瘤免疫研究的殿堂。
那个时候,我的免疫学知识完全是一片空白。从美国回来,我也没什么志向,想在北医躺平。可是,在陈老师的实验室是躺不平的。陈老师不停地鼓励我考博士。我说我看不懂当时的免疫学教科书,陈老师就拿出他的ImmunoBiology让我学习;考试前我不想复习英语,陈老师赶我回家复习,让我不要掉以轻心……。
2002年,在陈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Journal of Immunology杂志发表了题为Large Scale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Associated Antigens by Autoantibodies的文章。说个小插曲,文章被接受的那天,全实验室都非常高兴和兴奋。第二天一早,好像是个周六,我在去实验室的路上碰到陈老师,我看陈老师脸色不大好,就跟他说,“陈老师,咱们的文章被接受了,这是多高兴的一件事呀!“陈老师回我说,有什么高兴的,已经过去的事了。永远向前看,是陈老师的性格。
陈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治学的严谨、对细节的打磨和高度的自律。做学生的时候,总觉得他要求太高。而一旦自己独立工作,才体会到这些品质,对一个做科学研究的人,是多么重要。陈老师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如一日,早晨8点、中午2点,晚上7点到实验室,阅读文献,给学生修改论文,写教材。每周组会,进展汇报后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发表意见。对科学的追求贯穿在他的生命之中。
陈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同时给了学生各种发展机会。他为我们提供了国外进修的机会,鼓励我们积极申请科研基金,参加会议presentation,与国外学者交流。我始终记得,陈老师派我代表他去见Dr. Old的情景。点点滴滴,奠定了我事业发展的基础。
今年是陈老师诞辰90周年。与陈老师在一起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陈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导师陈慰峰院士-王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