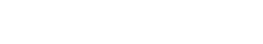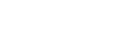父亲和他的收音机
父亲走了,他的小木桌和桌上那台有点老旧的收音机静静地在阳台的一角呆立着。每天清晨,只听到微风吹拂窗棱发出吱吱的声音,却再也听不到收音机里那个女播音员清晰圆润还时常夹杂一些噪音的伦敦腔。
父亲的生活非常规律。他有每天早晨收听英语新闻的习惯。这个习惯伴随了他几十年。从我上小学时候便是如此。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六点半晨练,七点打开收音机,七点-八点收听一小时的新闻播报,八点-九点便伏案阅读,书写或批改英文学术文献。
记得我上小学时侯(在他第一次出国之前),英语的听力资料和英文著作十分少见。他仅有的来源便是收听英文广播和阅读英文版的毛著。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台二手收音机,那便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电器。
每天天不亮,他便开始了收听广播。那时候家里只有一间房间,他怕吵醒我们,总是尽量地把音量调低。但我还是听到了那个伦敦腔和吱吱的噪音。我总嫌它吵,父亲便用他晨练时采的野花来哄我。那时的我哪里知道他学习和工作的不易。

后来他出国回来,带来一台新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的噪音少,好听多了。还可以收听外国音乐。但是每天早晨听到的,还是那个伦敦腔的新闻广播。我那时上初中,开始学英语了,知道那是英语广播。但是播音员的语速太快,听不懂。便问父亲,“听得明白吗?为啥不听听音乐,听新闻多乏味啊。“他笑笑,说听新闻对提高英语很有帮助。他出国以后,觉得自己和外国学者的差距很大。想要在国际学术领域和别人顺畅交流,必须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他说着,便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那里是他每天收听英语广播做的记录。里面有生词,有他认为精确的英文表达。他说听第一遍的时候可能跟不上,但是只要坚持多听,慢慢地便可以听懂了。他还告诉我,刚去澳洲留学时,因为他的口语和听力不好,曾经遭受过个别白人的冷眼。他却从此更加坚定了学好英语的想法。在他的鼓励下,我也照着他的样子,跟着他一起听。可是只坚持了几天,便觉得老听新闻没意思,就坚持不下去了。父亲也没有过多责备,依旧每天清晨开启他的收音机,收听英语广播,认真地做着记录。
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了他因重病住院的最后半年才不得不停下。
父亲走了多年,铺了一层薄尘的收音机静静的立在阳台的一角,每当微风轻轻吹动窗棱,发出吱吱的声响,仿佛那台老收音机又发出了噪音,久久不散。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陈慰峰院士-女儿陈进